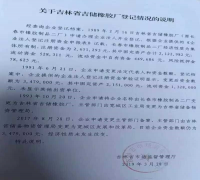- 先锋日报——先锋是一种态度,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
远山:我的创作生活
每天早起半小时,一生只做一件事。这是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几十年就这么过来了。
早上5点前起床,洗漱后,6点前出发。先坐地铁9号线,再换6号线,7点前到单位吃早饭。单位8点上班,我7点半之前,已经坐在办公室了。
我常常看到男女同事,都8点多了,才一手拿盒奶,一手攥个鸡蛋,嘴里还叼根油条,踩了两脚火似地,慌慌张张往办公室跑。领导偶尔撞见了,虽未喝斥,大都也自觉狼狈,牛奶、鸡蛋再也吃不进胃里,吃进胃里的油条也不是个滋味,老在胃里堵着。
我就感到了,“早起半小时”的好处。无论干什么,这一天,都胜似闲庭信步,看天上云卷云舒,也有了蔚蓝的心情。
难得毛主席和蒋介石都敬服的曾国藩,就特别反对“睡懒觉”。曾国藩有个“八为本”,其中之一就是: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并指斥:晏起为败家之凶德。治家不能“睡懒觉”,治军更要早早起床。李鸿章是曾国藩的爱足,“睡懒觉”也不能饶过。
鲁迅先生也是个热爱早起的人,上小学时,就用刀在自己的课桌上,深深地刻了一个“早”字。
那“早起半小时”干什么呢?这就与“一生只做一件事”有关了。这“一件事”,就是“写作”,或者叫“文学创作”。写一首小诗,记下几句感想,草录一个构思。而已。
实际上,半个小时,也干不了什么大事,但对我挺重要,挺有用的。虽然只是匆匆一个草稿,一个朦胧的想法,可待周末、节假日有了空闲,就可以好好斟酌、完善。把小毛孩养大,把毛坯房里里外外装修妥当。一首诗,一篇文,就和人见面了。
而今,告别了办公室,不用再早出晚归,再按时按点上下班了。“我的青春我作主”,成了“个体劳动者”,我仍坚持“早起”的老习惯。时间是自己的,笔是自己的,诗诗文文,长长短短,天南地北,信马由缰,想写啥写啥,想写到哪儿就写到哪儿。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万类霜天竞自由。
遥想远山当年。我从小数学就不错,总参加学校、公社和县里组织的“数学竞赛”,偶尔也能拿个奖回来。但我很早就当了“语文课代表”,从小学直到初中,再到高中,所以大学就考了中文系。
其实,1979年高考时,5门功课,我语文考得最差,只得了50分。原因是,那年没让写作文。作文考什么?让考生把作家何为的散文《第二次考试》,改写成“陈伊玲的故事”。望着奇怪的考题,我莫名其妙,就只得了“50分”。40多年过去了,我还和当年一样莫名其妙。
有这么出作文题的吗?这是在考作文吗?
好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很大度,很包容,硬是把我这个语文只考了“50分”的考生,给录取了。这大概就是命运吧。令我无比爱戴的母校,可能也认为那年的作文题,出得太“不着调”了。考“50分”,上中文系正合适。这样,稀里糊涂出作文题的老师,也可以从中反思一下。何为先生也高兴:大作家的代表作,是谁都可以改来改去的吗?
没改好“名家名作”,没写好“陈伊玲的故事”,没耽误我上中文系,更没能阻挡我热爱文学。那时“文革”刚刚结束,被禁锢了十年,960万平方公里的山川大地,神州十几亿男女老少,还有百怪千奇的文学艺术,都一轰而拥到了新刷的雪白起跑线上:我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万象更新,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
除了上课,我就往图书馆跑。在老家上中学时,我没见过图书馆。而且,我大学的图书馆,比王府井的百货大楼,都漂亮。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让我眼花缭乱。古今中外,那么多文学名著,逮住哪本算哪本,对我都是美味佳肴,都是宫廷玉液,都是法国大餐。
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虽然俄国的这位小说大师,很瞧不起比他年长264岁的,英国的这位戏剧大师。但丝毫也不影响,我对他们二位的同等热爱,双双痴迷。托翁《战争与和平》《童年少年青年》这样的长篇小说,莎翁《哈姆雷特》《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这样的悲喜剧,竟让我神魂颠倒,寝食难安。不到半年,我就戴上了近视眼镜。黑夜给了我一副黑框眼镜,我却戴着它读到天明。
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园丁集》,也让我长时间揣在书包里,有空就抄几段,不知不觉就抄了五六本。从中似乎寻到了“五·四”白话诗的源头。特别是依稀看到了,胡适《尝试集》,冰心《繁星》《春水》的师承。无比庆幸的是:泰戈尔复活,并催生了我那颗朦胧的诗心,让我更坚定地爱上了诗,成为痴情不改的诗歌爱好者,而且坚持不懈写了几十年。
我还爱往阅览室跑。阅览室也很大,三面玻璃窗,屋顶有一排排乳白色的灯管儿。这么好的光线,让我眩晕,让我感动。因为我的近视眼,日益加重,到哪儿都要先开灯。黑灯瞎火的,我伸手,就找不到五根指头。
阅览室订了好几百种报刊杂志,文学杂志也有百八十种。我经常看的有:《当代》《十月》《收获》《花城》《钟山》《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诗刊》《星星》,等等。
看到我特别喜欢的诗歌、散文,我就马上抄下来。有的小说,我也爱不释手,想抄但是篇幅太长了。想把有这篇小说的杂志,揣书包里偷走,我又干不了。主要是胆小。只有趁人不注意,把这篇小说撕下来,拿回去再细细品读。这样的偷鸡摸狗,不是很多,也就两三回。那也不好。如果别人想看那篇小说,就看不到了。我就立即洗手不干了。
发愤读书,振兴中华。我们那一批人,太热爱读书了,还有使命感。可又没钱买书……孔乙己认为:“偷书”不能算“偷”。
我有个同学,“偷书”被逮着了,给了个处分。他“检查”说:自己得了“幻想症”,跟哈姆雷特似的。学校认为他“耍赖”:你当“偷书贼”,跟“丹麦王子”有什么关系?这哪儿跟哪儿呀,学中文的,也不能胡说八道呀?其实,他的“检查”,还是挺深刻的,不一定是“胡说八道”。
还有一个大学生,要考研究生了,没钱买参考书。1981年4月的一个晚上,到西单新华书店去偷,让忠于职守的值班员逮了个正着。读书的学生嘛,哪儿干过这个,虽然之前也多次勘查过地形,“踩过点”,做过充分准备。还是被逮着了。逮着就逮着呗,赔点钱,给个处分,还能怎么着?
可读书人脸皮薄,他想跑,就拿随身带着的小锤子,和两个爱岗敬业的值班员搏斗。结果,打死一个,打伤一个。这个大学生,当年9月就被枪毙了。他是北京外语学院法语系七八级的,因为学习成绩连续三年“优秀”,直接跳班到七七级,正废寝忘食忙着“考研”哩。“研还没考”,“命就没有了”。
太让人痛心了,比早年被“打断腿”的孔乙己还惨。所以几十年了,我一直记着:他叫冯大兴。特殊的年代,特别的事。好在时代进步了,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教我们现代文学的王景山先生,好像是中文系的副主任。王先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闻一多的学生,研究鲁迅文学的专家。王先生认识很多当时正大红大火的作家,他和系里其他老师就经常请作家大腕们,来校给同学们演讲、作报告。
第一个请来的是王蒙。1957年“划右”后,王蒙曾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给王景山先生当过“助教”。梳大背头,戴黑框眼镜的王蒙,洋为中用,大搞“意识流”,在文科学生中,有很多“粉丝”。王蒙坐在讲台上,阶梯教室黑压压的,全是人。后面的人看不到王老师,大叫“站起来”。王蒙笑了:“还没动物园的猴好看哩。作家别见面,见面怂一半。要好看,可以请北京电影学院的明星。”大家哄堂大笑。
他还说:“我在给王景山先生当助教时,家里生活挺困难的,学校曾补助我200块钱。让我度过了难关。”又是哄堂大笑。王蒙文学课都讲什么了,我倒全忘了。
时隔20多年,2001年3月和2007年3月,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我曾两次采访过王蒙。王蒙是全国政协常委,那时我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社当记者。王老师有两句话,我一直记得。一句是:买官卖官比贪污受贿还可怕;一句是:领导比群众好糊弄。
2018年3月,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王蒙也来讲过。王老师80多岁了,身体和口才都挺好吧,不见老。会场乱糟糟的,王老师思路一点不乱。
继之而来的是刘绍棠。也梳大背头,戴黑框眼镜,派头丝毫不逊王蒙。刘绍棠说,他被打成“右派”后,本来也要到北京师院中文系当“助教”的,可是王蒙腿快先来了,他只好回老家通县(现在的通州区)劳动改造。谁想师院并非久留之地,很快王蒙就告别师院,去了新疆伊犁。八千里路云和月,戍边去也。
王蒙14岁入党,是个“红小鬼”;刘绍棠13岁发表小说,是个“神童”。重回文坛后,王蒙眼睛向外,拿来主义,在创作上“改革开放”,举“洋旗”。刘绍棠立足乡土,一亩三分地上打深井,讲“运河故事”,举的是“土旗”。一“洋”一“土”,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各有各的“看家本领”,各有各的“拿手戏”。东山上开花,西山上结果。谁也取代不了谁。好一派繁荣景象。
刘绍棠慷慨陈词:“在外国是土的,拿到中国就是洋的;在中国是土的,拿到外国就是洋的。土和洋是相对的,没有土就没有洋。越洋的就是越土的,越土的就是越洋的。所以,土就是洋,洋就是土。要洋为中用,不能邯郸学步。一句话:吃羊肉长人肉。”我还从没有听到,有谁把“土洋关系”,讲得如此淋漓透彻。刘绍棠还有四句文学口号:“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听着也很给力。
后来,我和几个同学去刘绍棠的“蝈笼斋”,拜访过他一次。
1985年夏天,北京作协在昌平一个叫“虎峪风景区”的地方,搞了一个文学培训班。我是学员,刘绍棠是老师。刘老师依然高谈阔论,大唱乡土文学的“高调”。那时,我已毕业,分到延庆中学当语文老师,业余写点东西。刘绍棠虽是大作家,看到北京郊区的文学爱好者,他又认识我,就十分热情。刘老师当面给了我很多指导,有时在报刊上发文章,也点点我的名字。
1994年,我出散文集,刘绍棠老师抱病给我写序。第一句话就是:“很多青年作家,尊敬地叫我老师,我都是盛情难却,实不敢当。可是利华(我的本名:刘利华)叫我老师,我并不觉得受之有愧。”刘老师对我真是偏爱厚爱。
我的老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周国华,为我这本书,曾专门录制过一期节目,刘绍棠老师又撑着病体,在他的“红帽子”书斋,接受专访,侃侃而谈了20多分钟,对后辈的殷殷鼓励之情,让我感动不已,至今不能忘怀。我的同学、北京大学教授张英,我的好友罗兴平、鲁雪雷、黄辉,还有一位摄影家朋友等,也盛情参加了这次节目,各自发表了真知灼见。
女作家张洁,也来师院讲过课。那时,我看过张老师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等小说。张老师讲了一件事,我和同学们听得心惊肉跳。大意是:张老师“入党”后,为了检验自己是不是忠诚坚定,假如落到敌人手里会不会叛变,她就学着刽子手的样子,把一根铁棍在炉子里烧红了,往自己撸起的胳膊、大腿上,一棍子一棍子地烫。听着“嗞嗞啦啦”的声音,望着袅袅的白烟,闻着缕缕的焦糊味儿……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雪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共产党人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钢筋铁骨”嘛,“老虎凳”“钉竹签儿”“灌辣椒水”,咱还没用哩。
听到这儿,好多同学大笑起来。而端庄秀气,说话温言细语的张洁老师,没有笑。她很认真,满面郑重,接着说:我身上流血了,疼得流汗了,我没有流眼泪,我没哭。大家又给张老师鼓掌,热烈鼓掌。张洁老师解释说:也许,我很幼稚,很傻,但我是真诚的。
张洁老师讲的这件事,还有她说的这一番话,比她任何一部作品,在我心中产生的冲击力都要强烈。为此,我去过上海龙华、南京雨花台、重庆渣滓洞、江西上饶集中营、贵州熄烽集中营……革命先辈们,面对反动派的屠刀,个个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有很多人出身豪门,上过大学,留过洋,穿长衫,戴金丝眼镜,本是可以当作家,当诗人,当大学教授,或者到国民党里当官发财的……起码不用钻山沟,穿草鞋,吃树皮,更不用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出生入死。
可革命先辈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自己身处那个年代,我究竟能不能经受如此严峻的考验呢?
这时候,我就又想起了张洁当年的那次讲座。而今,我们党已有9500多万党员,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像张洁那样,经常自己问问自己:在各种各样考验面前,能不能做到“绝对忠诚”?由此对张老师更生一分敬意。
人生是什么?有人说:人生是苦中作乐。我说:不,人生是与命运无休止的搏斗。这也是张洁老师的话。真是柔肠侠骨呀。是个好作家,也是个好党员。
老作家萧军自称“出土文物”,在他女儿的陪同下,也来学校讲过一次。他主要讲了萧红,讲了鲁迅先生。萧老师重点讲了,鲁迅先生对他和萧红的指导。他说:鲁迅先生心特细,帮他们改错别字,改病句。萧红的字写得小,还潦草,鲁迅先生看她的稿子,有时就帮她誊抄一遍。送朋友书,鲁迅先生打成一包,捆包的绳头都要用剪刀剪齐。大事小情,事必躬亲。要不,鲁迅先生55岁就病逝了,先生是累死的。鲁迅先生比很多人,活得都累。
香港著名诗人何达,和王景山老师是西南联大的同学,也被王老师请来,讲过一次诗歌。好像是初春,我们还穿着棉衣,60多岁的何达,却穿着T恤和短裤。一见面,就让我们刮目相看。先用笑声和掌声,表示钦佩。何达曾向闻一多、朱自清、艾青等大家,学习写诗,有一颗赤子心,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写的诗,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特别适合朗诵。记得何诗人,现场曾朗诵过几首。其中一首,叫《快乐的思想》。通俗易懂。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
《快乐的思想》
做每一件事情
都给它一个快乐的思想
就像把一盏盏灯点亮
砍柴的时候
想的是火的诞生
锄草的时候
想的是丰收在望
与你同行
想的是我们有共同的理想
与你分手
想的是重逢时的狂欢
著名作家刘心武、陈建功、李陀、孟伟哉等,也来校讲过。我和同学还请作家甘铁生讲过。转了好多弯儿,钻进北京一条古老的胡同,去请诗人食指,赶上他家里有人生病,就没有来。食指有一首诗,叫《相信未来》,好多同学都会背。有人就开玩笑说:就因为咱们老背诵“相信未来”,所以,食指才真“未来”----没有来。
我是土生土长的延庆人,小学、中学都是在偏僻的山村上的,读的书极少,基础太差。18岁上大学之前,从没有离开过延庆盆地。一睁眼,往哪儿看,都是山。眼界和胸襟,让沟沟梁梁,给缠裹住了。
所以,在师院中文系学习这4年,尽管我起五更爬半夜,头悬梁锥刺骨,却终未摘了“差等生”的帽子。是个“老大难”,重点“帮扶对象”。甚至,还被教文学概论的向锦江老师,严厉训斥过一回。和我同遭“训斥”的,光我们宿舍就有五六个。哲学我还补考过一次,才及格。
知道历史上有个勾践,几欲在宿舍挂个苦胆,每天舔一口。可惜,小小一个寝室,床上架床,住了7个同学。我担心,一个苦胆7个人都来舔,你一口我一口,一个礼拜就给舔没了。那年月,猪肉都很难吃到,猪苦胆更不好买。
教写作的老师,就是高明。他说:中文系的学生,应该会写东西。不会写东西,门门功课一百分,也不叫能耐。一句顶一万句。因为写作老师这一句话,救了我。让我在迷茫彷徨中,明白了天无绝人之路。
拉屎攥拳头:那我就写东西吧。好在我上中学时,爱写作文,有点基础,还写过一首顺口溜式的诗歌,让我在班里和学校,小小出过一回风头。只好先写诗歌。我白天写,晚上写,日产诗歌五六首。
请要好的同学“指点”,他们说:什么玩意儿?总这么拿着棍棒“指点”我的,有赵学功、谢久忠二位。但我并未被棍棒吓倒,反而愈挫愈奋。任尔东西南北风吼,我仍是每天五六首。好友怕我“疯了”,一边把碗里的肥肉片挟给我吃,一边“心疼”地安慰我说:好多写诗的,都是“神经病”。咱不写诗,没病没灾地活着,不也挺好吗?
我却固执地认为:我们的生活,不光有肥肉片,还必须有诗,有写诗的远山。
这样没黑没白干了一年,还真鼓捣出一些分行排列的“玩意儿”。1982年9月,《北京师范学院报》最先开眼,发现了我。把我写的一首欢迎新生入学的小诗,登在了“院报”上。题目叫《练就鹰的翅膀》。望着我的“处女作”,我觉得比个“处女”还娇美绰约。真是楚楚动人,视之怦然心动。居然,还给了我几块钱稿费。
看到了希望,尝到了甜头,我更来劲了。我的同学张文玺,是从房山来的,在“院刊”上,发了一首《暑假,我晒黑了》,又在《北京晚报》上,发了一首《三月,你好》。比我写得好,名气大。张文玺对我说:这么多写诗的同学,咱们成立个诗社吧。
讨论了一夜,主要是为叫什么“社名”,争执不下。后来,有个城里的同学说:就叫“雪浪”吧。那是个冬夜,老天下了一世界雪。一屋子年轻的诗人,群情激奋,个个满脑门子汗,跟刚刚吃过“麻辣火锅”似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雪浪”诗社,那个来呀来到。
张文玺牛牛地当了诗社社长。出了几期油印的《雪浪》诗刊,有些不大不小的影响。一日,张文玺社长说:咱们举办个诗歌竞赛吧。小诗人们都热烈响应,没几天,就征集了好几百首。然后评奖。校内校外找老师,找专家,找诗人,把作者名字捂上,公平公正嘛。没想到,我中了一等奖。题目叫《崭新的电车》,奖励我一个手提包。是真牛皮的,不像后来河北白沟卖的那种冒牌货。我现在还经常提着它,参加一些体面的高规格会议。
后来,我想了想,《崭新的电车》能获奖,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首诗,整体上采用了象征手法。直接受到了梁小斌《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还有王小妮一些诗歌的影响。间接上,我读了诗人艾青、戴望舒、徐志摩,臧克家、何其芳,读了诗人雷抒雁、流沙河、邵燕祥、叶文福,读了朦胧派诗人北岛、顾城、舒婷、芒克、江河、杨炼、徐敬亚、吕贵品,读了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彭邦桢、非马、席慕蓉……这一大批诗人的作品,也让我吃了很多营养液和激素。
还有一位兄长,叫鲁雪雷。我必须说几句。雪雷兄是堂堂北京四中的高材生,“文革”期间,他积极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上山下乡”到我们村。我正在上中学,在学校听不明白的课,经鲁老师一讲,我就懂了,他是我的“课外辅导员”。
我参加高考那年,雪雷兄已经回城了,他还经常给我寄“参考书”。我能考上大学,雪雷兄对我的帮助,超过我的很多老师。我刚到师院上学,雪雷兄就在甘家口,请我吃饭。还点了一条鱼。大概要花掉他半个月的工资。
雪雷兄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在我们村插队时,他就写诗。他听说,我爱上了写诗,不知从哪儿找了几本,北岛他们编的《今天》杂志,给我看。上面登了好多“朦胧诗”。我一头扎入《今天》杂志里,就像高尔基扑在了面包上。高尔基他们苏联人爱吃面包,我那时写诗正如饥似渴,像苏联人吃面包那样香。
雪雷兄还带我去中国美术馆,看了一次“星星画展”,也让我耳目一新,大开眼界。诗书画一体嘛,滋养了我的诗心。看得多了,写得多了,诗艺也有所长进,就冲出了校园。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发了一些现在看起来,比较可笑的“应景诗”。
中文系七七级的师兄张宏,是著名诗人张志民的公子,曾在《北京师范学院报》《北京日报》当过文艺编辑,编发过我不少诗,是我艰难摸索学诗路上的第一个“贵人”,引我入门上道儿的“启蒙老师”。
外国的诗人,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的诗,我也看过几本,总的感觉:诗还是应该读原文。因为诗不能翻译,一翻译就变味了。
都是汉语,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谁都翻译不了。简单的几句“口号诗”,比如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再比如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个字都动不了。只要动一个字,就会跑风漏气。气韵味道没有了,还叫诗?
中国诗都翻译不了,外国诗就更没法翻译了。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翻译家们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反正,自此我不怎么读外国诗了。我想学好了外文,再读不迟。
那年头,挺拿文学当回事,在校的大学生能发个作品,走路都不一样。
谢久忠他们班,有个李功达,在《人民文学》发了两篇小说。在我心目中,李功达就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同宿舍的一个同学,老家是平谷的,在《北京文学》发了一个短篇小说:《队长媳妇》。政教系一个漂亮女孩,马上就爱上了他。成了《队长媳妇》的“媳妇”。“漂亮女孩”家,还是城里的。只是平谷同学娶了城里媳妇,却再也没见他写小说了。后劲儿都跑到哪儿去了?我的大师兄。你在京城还好吗?
1983年7月,我从师院毕业,回到老家,在延庆中学当了4年语文教师。紧张的工作之余,仍然坚持写诗,还给学校的一个文学社,讲过一次“诗歌创作”。学生们挺爱听。
期间,我参加了延庆诗人连禾任社长的“七色花”诗社。成员有:王自明、张夙起、石中元、吴赤宇、谢久忠,还有我。一共7个人,都是男性。不定期搞点活动,谈谈诗歌,聊聊天,也喝喝酒。偶尔,“七色花”也到报纸、杂志上,联袂集体“绽放”一回。
诗社中的6位,皆我兄长,对我像小兄弟一样,倍加关爱呵护。阳光雨露予我最勤最多者,当属连禾老师。7人本职不同,性情各异,作品也自成面貌,却亲如手足。不管谁出集子,谁获奖,7个人都要想方设法凑齐了,相约举杯庆贺。海誓山盟一番。
好像是1984年,我在甘肃省武威市的《红柳》杂志上,发表了组诗《俺村的小伙儿喜欢写信》,有点反响。当年夏天,红柳杂志社便邀请我和三弟华夏,赶赴古称“凉州”的武威市,参加他们组织的文学笔会。
这次“凉州之行”,从延庆康庄站乘火车,走了两天两夜。没座位,站了一路,才抵达心驰神往的武威市。中国真大,火车真慢。实在扛不住了,我们就在地上坐一会儿,或躺一会儿。茫茫戈壁,浩瀚沙漠,一眼望不到边。马踏飞燕,月牙泉,让人魂牵梦萦。累是累,苦是苦,倒也饱览了风光,饱餐了“手把肉”,还结交了一批文朋诗友。
都挺能喝酒,都挺能吹牛。几百年也出不了几个的“文曲星”,齐聚甘肃省武威市开笔会来了。今夜无眠,今夜星光灿烂。从全国各地来了100多人,笔会规模气象不凡。
红柳杂志社办事,也不抠抠搜搜。临走,还把我和华夏的火车票给报销了。沿海发达城市也未必舍得。诗人“融点”低,比较容易激动。紧紧拉住亲人的手,我是一步三回头,泪眼朦胧望“红柳”。在你的毡房外,我唱断了琴弦。为了心中的“诗神”,我去了一个地方叫永远。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古凉州”那么多“千古绝唱”,不过“略输文采”,也就“稍逊风骚”,随着岁月的黄沙已经“俱往矣”。做不了“风流人物”,也不能沉醉在王翰、王昌龄、高适、岑参的酒杯里,妄自尊大,不思进取。
于是,我读了一些“新边塞诗”,比如闻捷、杨牧、周涛、昌耀、张子选、刘亮程,同时还发现了于坚、伊甸、曹剑、黄邦君、柳沄、海子等,也颇对我的胃口。搜来,悉数置于案上,生吞活剥,好一通饕餮美餐。
似乎有点感觉了,偶有灵感乍现时,乘兴写下的“长短句”,就一行行一队队,整齐排列在:《当代》《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山西文学》《当代诗歌》《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等,大大小小的报刊上。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创作的《写在党的旗帜上(组诗)》《走向1997》,还在《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等组织的诗歌征文评比中,分别获得三等奖和二等奖。
1994年,那是一个春天,幸得肖衍庆、齐颖二总编鼎力相助和支持,我的诗集《黑月亮 白月亮》上下两本,一本抒情诗集,一本爱情诗集,在同心出版社出版。受到著名诗人雷抒雁、高立林,著名诗评家张同吾,著名作家凸凹等老师,热情鼓励和肯定,并获得:北京首届写作艺术节优秀作品特等奖。诗人金蝉称我为“新乡土诗人”。
2022年,又是一个春天,为了喜迎“北京冬奥会”,作为“冬奥会”的礼品书,北京出版集团出版了我的诗集《山一程 水一程》。有300多首。
我的老领导,作家、诗人石中元,满怀深情和殷切希望,专门撰写了两篇热情洋溢的长篇评论:《人民诗人远山》《一首歌是一面旗》,给我加油鼓劲和积极推介。
我的老朋友,作家郭嘉兴,放下手头的公务,夜以继日,加班加点,赶写出长篇评论:《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为我擂鼓助阵。
“人民网”“中国作家网”等也刊发了消息和文章。不“甩开膀子加油干”,我都对不住,这么多关爱厚爱我的领导和亲朋好友。
1992年,由著名作家中杰英推荐,我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
2003年,由著名诗人雷抒雁推荐,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雷抒雁老师在推荐词中说:远山是跨世纪的抒情诗人,他的作品是一代人的心灵吟唱。
2016年,全党开展“两学一做”活动,为了检验学习效果,以推向深入,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纪工委在101个部委,组织了一次全规模的比赛。领导让我牵头这件事。决赛的时候,需要插播两首主旋律歌曲。我们找了十几首,领导都认为不合适。有位领导说:你不是会写诗嘛,赶紧写两首。赶鸭子上架,没办法,我憋了整整一夜,写出了两首似是而非的所谓歌词。
第二天,又研究这件事,领导问:歌词写好了?我就鼓起勇气,念了一首《明白人 清白人》,念了一首《使命担当》。没想到,领导和同事都鼓掌。领导说:光听你念,就挺带劲儿,小子行呀。赶紧找人谱曲,找人唱。曲是青年作曲家王艺歌谱的,演唱是武警部队女中音歌唱家刘子旗。两位艺术家,真是德艺双馨,连工委、纪工委一口水,都没有喝,就完成了任务。
特别是刘子旗老师,不仅演唱录音不要钱,还自掏腰包,花了百八十万,把这两首歌,拍成了MV。军人就是能奉献。刘子旗家三代军人,更是特别能奉献。“正气歌”就应该让这样“不爱钱”的军旅歌手唱。“决赛”播放这两首歌曲时,现场300多位部长、司局长,听得柔肠百转,热泪盈眶。“决赛”刚结束,工委领导就和我亲切握手,热烈拥抱,合影留念,并高兴地说:可给咱工委长脸了。
后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看到了这两首歌的MV,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批示中央主流媒体播放。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还把这两首歌,作为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的音像资料,永久收藏。《使命担当》歌曲MV,还荣获安徽省“五个一工程”优秀文艺作品奖。中央纪委的老干部,还把《明白人 清白人》歌曲,编排成了集体舞,边舞蹈边演唱。
为了配合本职工作或应约,这些年,我先后写了20多首歌词,作曲家王黎光、朱培华、刘跃强、段泽兴、王艺歌、周海涛、陈利民、蒙根等谱曲,歌唱家阎维文、汤非、张琳、吕薇、刘子旗、李娜、崔子格、舒婷、黄玮,电影演员胡静等,都演唱过。其中,我作词,王黎光谱曲,刘子旗演唱的歌曲《红色南昌 英雄南昌》,曾荣获江西省“五个一工程”优秀文艺作品奖;我作词,周海涛谱曲,刘子旗演唱的歌曲《我为祖国守护一座岛》,曾荣获全球华语音乐金曲榜冠军。
2017年,我作词,张廷亮谱曲的《在田野 在山岗》,在网上发布后,河南电视台12位著名节目主持人,联袂集体演唱,并拍成了MV,在河南电视台连续播放,为助力全省扶贫攻坚,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河南省直机关、河南省辉县市在庆祝建党96周年、97周年“党旗耀太行”等文艺晚会上,曾有数十名歌手和“驻村第一书记”集体联合演唱,场面盛大,气氛热烈。四川省广安市电视台也把这首歌,拍成了MV,作为该市电视台,扶贫攻坚电视节目的主题歌,长期播放。
好像也是2017年,好友虞宝才,在我老家延庆当纪委书记。虞书记想结合延庆的特点,创作一首《忠诚卫士之歌》,供区纪委在开大会,搞活动的时候,大家唱一唱,以鼓舞士气,振奋精神。高唱“正气歌”,“打虎拍蝇”劲更足。
面向全区,大约征集了上百首歌词,宝才选出十多首给我,让我帮忙改出一二首,再找人谱曲演唱。我翻来覆去看,觉得没法改,就另写了一首,供虞书记选择。最后,他们就请延庆著名作曲家史长江,把我写的《忠诚卫士之歌》,谱了曲。虞书记带领全区纪检监察干部大合唱,还拍成了MV,在区电视台、区会展中心广场,滚动播放。
直到2018年,虞宝才书记调离延庆,回到城里后,这首歌才立马给停播了。播放了一年多吧,还是有不少人学会了,能够放声歌唱。“正气歌”虽停播了,而“打虎拍蝇”,只有“进行曲”,没有“休止符”。不可沽名学霸王。
为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我作词,朱培华谱曲,倾情创作的献礼歌曲《人心是咱高举的旗》,由著名歌唱家阎维文、殷秀梅男女声携手演唱,也正在紧张录制中,并将拍摄成歌曲MV。
自己写的诗,被人谱了曲,满世界去唱,总归是件大好事。而且,我还听人说:音乐是最高级的艺术,最能直抵人心。那就让我的一首首诗,乘着悠扬甜美的歌声,去温润人们的生活,陶醉人们的心灵吧。
写诗的同时,我也写小说。我一度非常痴迷:莫言的红高粱系列,阿城的遍地风流系列,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李锐的厚土——吕梁印象系列,阎连科的耙耧山脉系列,杨争光的黄土高原系列,马原、扎西达娃的高天藏地系列,刘恒的新京味小说系列,王祥夫的好峁杂录系列,曹乃谦的温家窑风景系列,刘庆邦的走窑汉系列……还有阿成的“年关六赋”,李佩甫的“红蚂蚱 绿蚂蚱” ……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原始野性,沾泥带土,直逼生活。借用阿成一篇小说的标题,来描述的话,叫作:胡天胡地风骚。
诸人诸作,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狼吞虎咽,受益匪浅。我的小说创作,不可能不受到他们的浸染和牵引。
应该是1995年开春,我写了一个30000多字的中篇,名字叫《红颜》,有点儿狐媚妖气。故事一半缘自从老家听到的一个真事,又兑入一半的联想。用400字一页的稿纸写的,装了满满一书包,骑着自行车,兴冲冲,就给《青年文学》杂志社副总编赵日升老师,送去了。仿佛过了十几天,赵老师约我过去说:写得还可以,就是太长。先压缩到8000字以内,再拿来。
下班回到宿舍,半夜三更,披衣起身,遵照赵老师的指令,几欲挥刀,可眼望自己心爱的“红颜”,怎么也下不了手,砍哪儿我都不忍,我先自“心如刀绞”。我的心血,我的骨肉呀。虎毒不食子。我是属牛的,吃草,不吃“红颜”。
正当我倍受煎熬,痛苦不堪的时候,延庆好友乔雨、曹金刚着手编辑《延庆文学作品选》,我就把“含在嘴里怕化了”的《红颜》,从嘴里抠出来,给了他们。老家的二位朋友,敢下手,不由分说,就把30000字,折腾成了8000字。倒不是一砍三段,或者大卸八块,而是把“红颜”囫囵个吊在火炉上,像烤鸭,烤乳猪那样,烧烤烘干。把活色生香的当代“红颜”,“抽巴”成了长沙马王堆的辛追夫人。骨架还有,妩媚风流已荡然无存了。乌呼,自古红颜多薄命。
后来,看到《延庆文学作品选》,也就20多万字,收了五、六十人的作品,不可能发我一个人30000字。这样一想,也就心平气和了。让我捶胸顿足的,只是:30000字的《红颜》原稿,莫名地遗失了。也许是,落到人贩子手里,漂洋过海,不幸卖到国外去了。
2006年第2期,山西省大同市的《北岳》杂志,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毒日头》。该刊总编、著名作家王祥夫说:原来,以为你是个诗人,没想到,还会写小说。
2015年春天,我到河南出差,省纪委的领导给我讲了一个案子,故事挺传奇的,我就此演义成个短篇小说,取名《十日谈》,发在了2016年第2期《北京文学》上。编辑张颐雯在“推荐语”中说:县委书记收到了神秘短信,其中秘密耐人寻味。他曾经做过些什么?他又怕了什么?他对神秘短信的追根究底,会有什么结局,会将自己带到哪里去?小说以诡异的视角,揭开了中国官场的隐秘一角。
2015年以后,我在《中国纪检监察报》连续发了三篇小小说:《杀羊》《失眠症》《神算耿半仙》,全被《小说选刊》转载。非常感谢编辑戴希老师,他有一颗热心,有一双慧眼。《杀羊》同时被《微型小说选刊》转载,收入《新中国70年微型小说选》,并被教育部和安徽省、四川省等好几个地方,用作“高考阅读训练”的考题。那考题出的,连我这个作者,也回答不了。真难为孩子们了。
《杀羊》《神算耿半仙》,还先后获得《小说选刊》组织的微型小说征文,优秀作品二等奖和三等奖。2021年,我创作的小小说《百货大楼》,又获得《小说选刊》组织的微型小说征文,优秀作品优胜奖。
写小说,给我带来快乐的同时,偶也平白无故,给我增添了烦恼。
比如,我的短篇小说《千里马之死》《难言之隐》,尽管我采用了变形夸张的手法,有点像荒诞派。可发表后,还是有人对号入座,认为我在利用小说,含沙射影,讽刺挖苦他,从此不理我了,暗暗地生闷气。文化人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儿多得像筛子孔,而且小得如针鼻儿。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
其实,我写小说,谁也“不影射”,谁也“不讽刺”,谁也“不挖苦”。如果哪位看官,真从我的小说中,读出“影射”的话,那一定是,我在“影射自己”,我在“自嘲”。您千万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更别和远山“找茬儿闹别扭”。我不明白,您还不明白吗?
我很善良,我也很友好。我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亲密朋友。漫无目的,和“假想敌”较劲,是精神紧张,“抑郁症”的前兆。谢天谢地,阿门。
写诗写小说之余,我也顺手写点散文。无论是写人记事,还是抒情,我都不知不觉,学习了鲁迅、朱自清先生,效仿了汪曾祺、贾平凹、何立伟、凸凹几位老师的路数和写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因此,有的作品受到好评,有的作品还得了奖。
比如,1995年,我发表在《科技日报》副刊上的散文《大年三十贴红门儿》,获得了“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评比”二等奖。
比如,2001年,我发表在《三峡晚报》副刊上的散文《让生活诗意起来》,获得了全国散文征文二等奖。
比如,2002年,我发表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副刊上的散文《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获得了河南省《纪检与监察》杂志组织的全国散文征文一等奖。
再比如,2016年3月,我发表在《学习时报》副刊上的随笔:《我爱读“党章”》,也广受好评,有上百家报刊、网站纷纷转载。中央纪委、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更是当面给我鼓励和赞许。中央纪委一位领导说:你写的《我爱读“党章”》,我看了好几遍。为了强化记忆,我还在电脑上自己敲了一遍。安徽阜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周建华,还拿着我的这篇文章,给全校师生作了《怎么学习“党章”》的辅导报告。
1994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
2008年,我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社工作时,报社出版了一套丛书,有我一本散文集《天朗气清》。一套十多本,我这本书字数最多,定价最高,但是卖得最快。上架没几天,就销售一空。想买这套丛书的人,一看没有我的《天朗气清》,大多就不买了。书店的经理紧急找到我,要把出版社给我的一百本赠书买走,以期为这套丛书发挥“带货促销”的作用。
著名作家刘绍棠老师曾专门撰文,评价说:远山深挖历史文化,感悟风土人情,创作出的散文、小说作品,蕴藉深厚,读来耐人寻味,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是“乡土文学”创作又一重要成果。
曾任《北京日报郊区版》文艺副刊主编的著名作家王葆春老师,也撰文称赞我的散文:“旱香瓜儿--另个味儿。”
我不打麻将,不玩牌,也不会唱歌跳舞,上班之余,坚持文学创作,是我几十年的唯一爱好。不盲目艳羡:聪明人脑瓜儿好使,多才多艺。常反躬自省:本就天生愚钝,弱智低能。只得老鸹喯牛眼,专凿一门。
写诗作文,孜孜以求,虽没有多大成绩,倒也自娱自乐。往大了说,可以概括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利于家庭团结,也有利于社会和谐。总之,是积极健康的,百分之百的“正能量”。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何乐而不为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向未来,书写精彩。

作者远山简介
远山,本名刘利华。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北京市延庆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副书记。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当代》《十月》《散文》《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山西文学》《当代诗歌》等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出版《黑月亮 白月亮》《天朗气清》《山一程 水一程》等文学作品集5种,300余万字。有30余篇(首)小说、散文和诗歌获《人民日报》《小说选刊》“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选”和江西省、安徽省“五个一工程”等文学奖。被称为“跨世纪的抒情诗人”,作品被称为“一代人的心灵吟唱”。近年,他创作了一批歌词,广为传唱,受到了听众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