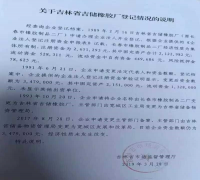岁月长 情怀老 思念新
(序 )
远 山
谁的声音那么大
千里外也听得清
蟋蟀唱起摇篮曲
满池荷花侧耳听
相聚时 分离时 都抱紧
咫尺远 天涯近 故土亲
翻阅了四季
拨动着心琴
忧是夏意
愁是秋心
二十多年前,曹克明当江苏省纪委书记的时候,我曾多次到过江苏,江苏省13个地级市我几乎都跑遍了。
纪检监察系统的人,没有不知道曹克明的。在我们党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活着时就成为全党学习楷模的正部级领导干部,曹克明是第一位。恐怕也是唯一的一位。曹克明书记是我们党反腐败斗争进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传奇英雄。2014年9月2日,曹克明去世时,习近平总书记、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深切缅怀。
别梦依稀咒逝川, 回首二十二年前。我还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社,当编委、要闻部主任。我每次到江苏采访,曹书记百忙之中,都要见见我,并让人陪我到下面市县跑一跑。跑得多了,就对江苏生出感情,也交了不少朋友。有人便诱我到江苏落户,甚至张落着在苏锡常给我安排个工作。 我动过心,却并未行动。心里暗暗将江苏当成“第二故乡”吧。
其间,有幸去过一次宿迁市泗阳县,就结识了该县年轻的县纪委常委张家龙。张家龙一表人才,玉树临风,容貌甚伟,一笑俩酒窝儿。话不多说,性格却豪爽,待人极热情。端起酒杯,总变着法让你喝好。宿迁是美酒之乡,以前的“洋河”“双沟”,现在的“海之蓝”“天之蓝”“梦之蓝”,均出自那块风水宝地。这些老酒新酒,都是咱中国人爱喝的上好佳酿。
张家龙常委一手挥舞利剑,打虎拍蝇;一手摇曳妙笔,写反腐倡廉的文章。
接触多了,我才知道,张家龙还是一个热爱诗文,喜欢写作的“文学爱好者”。多年来,他忙里偷闲,一直坚持诗歌和散文创作。这次,看到他的散文集《冬天里的成子湖》样稿,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作为年长他几岁的老朋友,看到他为古老乡村 ,为养育了我们的父老乡亲,浓墨重彩,诗意书写,望月抚琴,深情吟唱,不知不觉,也掀动了我内心深处,思乡想家的情感涟漪复波涛。
从江苏地图上看,成子湖像是刺绣在洪泽湖衣角上的一枚修长的柳叶 。将成子湖呼作“柳叶湖”,似也是可以的
江苏是鱼米之乡嘛,“柳叶湖”这样的湖泊,随处可见。我没有去过成子湖,却游览过江苏很多有名没名的湖泊。湖或大或小,一律清澈、闲适而澄静。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鸽哨鹤鸣唱得好听,也收获菱米鱼虾,网一世界莲花白鸥、渔歌和粼粼诗情。微风吹过,碧波一浪一浪漾过来,不紧不慢地拍打着沙滩和堤岸,如同母亲哼唱着歌谣,一辈辈悠扬着朴素而浪漫的村庄。
自然而然,这也就启蒙了张家龙这样一批有灵性的孩子,让他们长大以后,既能够杖剑反腐除恶,也会兴意昂扬地吟诗作文。
多少年来,生活在成子湖畔的父老乡亲,胼手砥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坚韧自持,顽强地活着。张家龙祖辈父辈也如斯不怠,他们在一个叫范家湖的小村庄筑居,耕作,炊爨,侍弄生计,繁衍生息。范家湖的田园湖波,冷冷暖暖着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张家龙,皴染氤氲了他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
所以,也就有了张家龙足足10万多字的乡情乡愁散文集:《冬天里的成子湖》。
在那弯弯的田埂上和贫瘠的年代里,张家龙神奇的艺术多棱镜里,都变幻出怎样的奇光异彩呢:他同龄的一代人的绚丽梦境和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画卷的集体眷恋,他乡情乡愁乡思冲洗出的模糊又清晰的记忆拓片。张家龙是在成子湖边的农村出生长大的,后来外出读书求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再后来,他离开钟爱的讲台,做了反腐倡廉党的忠诚卫士。
繁忙的工作之余,张家龙笔耕不辍,家乡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是他笔下活生生的素材:门前的柿子树、沟崖的野菊花、村头的老砖井、树杈的马蜂窝、农家的大石磨、香甜的槐花饼、紫红的桑葚果、家养的大花猫、忠实的看家狗、嫩绿的榆树钱、狭窄的小木船、温暖的压岁钱、年前的猪血汤、知青的口琴曲……朝花夕拾,情深意长;娓娓道来,亲切动人。
掩卷而思,我似有以下几个感想:
乡情是一杯盛满无限心绪的陈年老酒,年份越久远,味道越淳厚。
风土人情,也许是一个地方绵长浓烈的老窖,亲情更是让这沁人心脾的香辣,不断酝酿发酵无可替代的酒引子。张家龙细腻贴切的笔触,讲述的是家事,倾吐的是真情,咏唱的是心曲。
张家龙在《沾着泪水的烧饼》中写到:“那是1963年麦子刚抽穗的时节,母亲带着我10岁的哥哥,去8里外的公社医院,为他挖脚上长了半年的‘鸡眼’。因为哥哥走路时‘鸡眼’太疼,母子俩坐在路边歇了一歇又一歇。快晌午时,才到公社所在地的街头。
当母亲拉着我哥哥的小手,经过卖烧饼的店铺门口,哥哥停下脚步,盯住那一摞黄亮亮的烧饼,直往肚子里咽口水。母亲使劲拉他,他还是站在那里,不肯挪动半步。母亲摸摸他的头,轻声地说:乖乖,妈妈手里只有两毛钱!这可是为你挖脚上‘鸡眼’的钱呀!不挖掉鸡眼,你怎么走路上学呀?哥哥低着头,一声不吭,眼睛还是盯着面前香味四溢的烧饼。
母亲的心里,正为没钱买块烧饼给自己的孩子而犯难!过了一会儿,哥哥用瘦弱的小手,拉住母亲的胳膊,把黑瘦的小脸紧紧地贴在母亲的肩头,小声地对母亲说:妈妈,买一块烧饼吧,回家我自己想法子,剜掉‘鸡眼’。哥哥说着,眼泪便落在母亲的手背上。母亲的心软了,便从旧手帕里,拿出那张带着汗水和体温的两毛钱,递给了卖烧饼的老奶奶,哥哥从老奶奶手里接过两块烧饼,脸上漾起的笑容,把挂在腮帮上的泪珠,抖落在这黄亮亮香喷喷的烧饼上。他顾不得脚上‘鸡眼’的疼痛,笑着说:妈妈,我现在不饿,把烧饼拿回家,大家一起吃吧!说着,两只黑瘦的小手,紧紧地把两块烧饼,抱在怀里。”
饥饿年代,母子俩不同寻常的这样一件小事,经过张家龙绘声绘色的叙说,读来感人至深,令我喟然长叹。
乡愁是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越是一针一线缝补,越是锥心刺肺般疼痛。
没有埋葬过亲人的土地,不算故乡;没有经历过亲情离别的村庄,不能算是老家;没有在艰难困苦中一起生活过的亲人,不会成为至爱。张家龙的乡情乡愁不是古道西风瘦马,不是断肠人在天涯,而是在少年泪水中流淌的忧伤和怅然。
《黄土情深》,是张家龙怀念父亲的:“我和弟弟相差不到两周岁,我们出生的时候家里特别穷,布是凭票供应的。我们俩用块尿布都很困难,父亲就隔三岔五,步行二里多路,到高松河东的沙土地,去挑细细的黄沙土回家,晒干后堆在墙角。晚上,把细沙土敷在两块尿布中间,来吸收尿液。这样,整夜不换尿布,也不会有大量的尿液,浸泡我们的屁股。母亲说,冬天,父亲怕我们受凉,他就把冰凉的细沙土,先放在怀里焐热了,再放到我们屁股下面。那带着父亲体温的黄沙土,不仅给我和弟弟一个体贴而又温馨的生长条件,更是在我们的骨血里,融入了和黄土一样纯朴憨厚的基因,以致于我们长大了,走上了工作岗位,仍然心系那片黄土,仍努力地为报答生活在那片黄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尽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十年前那个秋天,柿子红了,凉风吹黄了老宅上那棵银杏树叶,我七十九岁的父亲突然离去。下葬那天,当父亲的棺材停放在墓穴旁,等待安葬时,我沿着墓穴的斜坡,双膝跪地,从即将掩埋父亲的黄土坑里,颤抖地抓起一把黄土,豆大的泪珠滴落在我的手背上,顺着指逢,浸湿了掌心里的黄土。父亲几乎不识字,我无法想像他八岁时,从爷爷墓穴里抓起那把黄土时,心里有多疼多痛,但是父亲离开我们这十年,我把从他墓穴里抓的那把黄土,一直珍藏在我书柜的底部,偶尔看一看,摸一摸,对着它说上几句话,诉上几句苦,我在心里计划着,等我老去那天,一定让我的子孙,把我珍藏的那把属于父亲的黄土,撒在我的骨灰之上,让我永远和父亲依偎在一起。”
乡思是一件时时唤醒追忆,包浆细釉的旧瓷,越是擦拭,越是耀眼灼心般地明亮。
那一辈辈,在成子湖边筚路蓝缕的日子,已渐渐遥远;那一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岁月,已成昨天。我们今天怀念和思考的,何止逝去的那些人和事?张家龙也写到了:那成片空置的老屋,那不再炊烟袅袅的村庄,那机器哑巴般不吭不哈的砖厂,那寂寞小学校孤立的篮球架,那打麦场上再也看不到了的老电影,那牛棚里孑然老去的说书人……
还有乡下老家那悄悄散去的浓浓年味,也热辣辣地缠绵在张家龙魂牵梦萦的乡思里:“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苏北的农村,到了寒冷的冬季,从田里闲下来的男女老少,习惯聚集在生产队的牛房里,妇女和姑娘们一起做针线,男人们忙着编毛窝鞋或是搓绳子,孩子们一边烤火,一边专注地从牛槽底部,捡拾那些遗落的黄豆粒子,放在火堆边,烧得香喷喷地分着吃。
腊月二十三这天,是生产队牛房里人最多,最热闹的一天。不论是刮大风,还是下大雪,老队长都会在中饭后,带领几个壮劳力,从集体的大猪圈里,抓出两头膘肥体胖的大黑猪,杀了分给每家过年。
这一天,也是生产队里一百六十多口人,整整盼了一年的日子。孩子们早早地吃了中饭,跑去牛房里,抢占有利的地形,等着看热闹 。大人们则互相打听:今年杀的是‘子猪’,还是‘大老公’?这‘大老公’,都是三年以上配种用的‘老陈货’,它的皮厚肉腻,一时半会难以煮透,就是干木柴大火加细火,也得足足煮上半天,才能勉强煮熟。最受乡亲们欢迎的,就是养了一年出头的两百斤左右的‘子猪’,‘子猪’的肉既细嫩又喷香,尤其它身上厚厚的肥膘肉,是最受乡亲们欢迎的。
大人们担心刚分到家的新鲜猪肉,被猫偷吃了,便赶紧用长长的麻绳,把肉吊挂在堂屋的二道梁上。 猫儿盯着猪肉,叫上一遍又一遍,有些馋嘴猫跳起来,抓上门框又跳下来,急得团团打转……”
年代虽远去了,这暖人的故事情节,却在张家龙《乡村里的年味中》,电影似的一幕幕回放,让人如临其境。
张家龙的散文,文字亲切质朴,纯粹干净,俚语土话,恰到好处,没有过多的修饰雕琢;风物刻画,细致入微,生机盎然;记人述事,有条不紊,妙趣横生。读张家龙的散文,就像在黑夜中行走,忽然有人擦燃了一根火柴,霎时点起了一团光。尽管这光很微弱,却在心头蹿动一团亮,让人看见了回家的路。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说过:诗人的天职是返乡。也就是说:不管我们走多远,也不该忘记了我们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
不能不说,农家出身的张家龙,是特别勤奋的。他利用业余时间,读诗写诗,自2000年开始,坚持了二十多年。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了诸多诗歌作品,在宿迁乃至江苏诗歌届,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位写散文的好手,善于用简洁的文字,引领读者,流连忘返于熟悉的故乡,回望迤逦时光里的一抹水墨烟霞,赏阅古色古香一笔写意的村庄,品读一个游子抑扬顿挫的心灵史。
读张家龙的散文,就好像同他喝酒聊天。酒酣耳热之际,竟唤醒了,我对江苏这么多亲切美好的记忆。
2001年,那是一个春天 ,我又到江苏出差。江南热得早,我就穿了件半袖T恤。谁知突然变天,下起了雨,气温一下子降了10多度。省纪委秘书长很快给我拿来了一件雅戈尔长袖衫,特意对我说:这是曹克明书记专门给你买的。赶紧穿上吧,别感冒了。顿时,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
2022年,又是一个春天,我宅在北京竹里馆,躲避新冠疫情。好像北归的燕子,衔来江南一树春光,我就收到了老友张家龙的散文集《冬天里的成子湖》。心中大悦,豁然开朗。夜以继日捧读,又是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顿觉:冬去春来,鸟语花香;开窗“鹧鸪天”,关门“满庭芳”。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
离家路 归乡路 无止尽
岁月长 情怀老 思念新
改变了模样
斑白了双鬓
不改乡音
不忘初心
我想念“我的第二故乡”,我想念江苏的亲朋好友们。屈指算来,我已有十五、六年,没有到过故地江苏了。
待死磨烂缠的新冠疫情过去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不再打仗了,台湾也和平回归了……总之,这个地球消停了,天下无贼,让世界充满爱。甭管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都能像哥们儿似的,有话好好说,遇事能够“换位思考”,多点“他人意识”,真正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见面了,不是“乌眼鸡”,不是“狗不理”,而是相视一笑,而是热烈握手,开怀拥抱,甚至“蹭蹭脸”,“吻吻手背”啥的。亲不亲,咱们都是一个小小寰球上,活得都挺不容易的人嘛。与其鱼死网破,不如合作共赢。
到了那个“平安无事喽”的时候,我还想再到江苏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吃一餐汤汤水水的“淮扬菜”,外加一盘南京的“咸水鸭”,一盘长江里的刀鱼或河豚,一盘阳澄湖的大闸蟹,一盘盱眙湖的小龙虾,一盘南京六合区的蟹黄灌淌包……自己花钱,丰盛一点。但也万不可奢靡,力争“光盘行动”。
届时,我一定要把心心念念,却多年只在梦里见面的老朋友们都约来,围成一个大大的圆桌,喝一瓶“海之蓝”,喝一瓶“天之蓝”,再喝一瓶“梦之蓝”。 亲朋好友们,咱谁也别端着,谁也别偷懒耍滑,都敞开心扉,放开酒量。把“海天梦”,全部喝成满世界的诗情画意,你往哪儿看,皆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色”。
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那该是多么浪漫抒情的人生啊。
梦里不知身是客,酒不醉人人自醉。纸短情长,感同身受。一句一句,却是掏心掏肺的话。
谨此为序,难表万一。
2022年初夏
于北京竹里馆
作者远山简介:

远山,本名刘利华。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理事。曾任北京市延庆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社副社长、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副书记。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当代》《十月》《散文》《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山西文学》《当代诗歌》等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出版《黑月亮 白月亮》《天朗气清》《山一程 水一程》等文学作品集5种,300余万字。有30余篇(首)小说、散文和诗歌获《人民日报》《小说选刊》“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选”和江西省、安徽省“五个一工程”等文学奖。被称为“跨世纪的抒情诗人”,作品被称为“一代人的心灵吟唱”。近年,他创作了一批歌词,广为传唱,深受听众的喜爱。